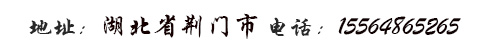四个男人刀尖下的,软肋和眼泪
|
北京中科医院诈骗曝光 http://baidianfeng.39.net/a_yqhg/160710/4895891.html 自古刀剑不分伯仲,但与剑的侠骨相比,刀多了几分匪气。于是剑留在了历史与武侠小说,而刀却贯穿古今。 到了现在,擅用到的男人,除了流氓就是厨子。厨子是个用灵魂驱动身体工作的人,哪怕AI取代了所有工种,我们也希望这个世界上仍有刀客般的厨子。 刀呢,还真的挺像人——除了锋利,还得舒服 摄影:FrancoisTrezin 阿基师 “玩菜刀的有了礼貌,就不大一样了” 本名郑衍基,台湾人,64岁 国宝级御厨,台湾省最具知名度厨师、烹饪节目制作人及主持人。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三任总统官邸的御厨,曾获得多个国际奖项,担任国宾大饭店行政总主厨。 在台湾,阿基师不止是个厨师,也不止是个明星,他已是正儿八经的人生导师。看他主持的节目,如同读刘墉的书,点点滴滴都是鸡汤。比如他在节目中用的刀,不是他常用的中餐刀,而是加了一点点西洋文化的刀。他说,那把刀很尖很细,有了可以表现的味道。 什么叫“刻画人性”?都在刀尖上展露。 阿基师做节目,眼睛是不看刀的。他得盯着镜头或艺人,和摄影棚的所有人都在互动。切菜切成大块时,他动作很快。切得很细时,他的刀变得很慢。但阿基师的目光,永远是在和观众交流。他说,如果你不看观众,人家会觉得你不礼貌。节目制作方都喜欢阿基师。在厨师界,很少有人能做到他这样——盲切。刀是跟着心走的。 这可不是一般的表演。阿基师说,刀的事,不能随便唬弄的。他今年64岁,玩刀玩了45年了。做学徒时,他也是经常受伤的。受伤后的第一个动作,失去找切下来的皮肉掉哪儿了。没找到,就拼命去吸伤口。如果找到皮,赶紧用口水湿润湿润,粘回去,风一吹,伤口就干了。实在不行,就用传统火柴盒上墨色的那一片纸,泡湿,缠在伤口上,以此隔绝细菌。这是好多年前的做法了。现在呢,如果阿基师的学徒受伤,他就掏出三秒胶,一粘就回去了。 在阿基师学厨的那个年代,用刀不仅比现在危险,还很不上进。 他是长子。父亲是从大陆撤到台湾的,原本期待他学有所成,再回大陆光宗耀祖。但阿基师的兴趣却不是读书——那时也没什么书可读。“师傅的菜刀,美发师的理发刀,裁缝的剪刀。在我年轻的时候,这三把刀是最不被认同的。”谁家有女儿,绝不嫁给这三种人做老婆的。不但收入微薄,还总是对别人鞠躬哈腰。所以阿基师是受了委屈,受了苦,入了这一行的。结果,一撑一眨眼,几十年过去了。观念改变也就是一瞬间。鞠躬哈腰,变成了礼貌。 玩菜刀的有了礼貌,就不大一样了。 “阿基师赚了很多钱。”——他讲话,不说“我”,称呼自己“阿基师”——“可是生活品味很单纯的。”他坚持不吃偏激的食物,不喝饮料,因为饮料会破坏厨师的味觉。他不抽烟不喝酒,更不吃槟榔。“如果阿基师抽烟吃槟榔,现在跟你讲话,满嘴槟榔垢、烟垢,总是不雅观嘛!”无论在哪里做表演,阿基师都把自己收拾得利落干净。其他厨师可能比较不修边幅,但阿基师给人的感觉,永远是清新、清洁、利落的。 阿基师能做到这样,全靠背后有个定得住的太太。有年母亲节,阿基师管理的十三家五星级酒店,当天收入破九千万。他回家跟太太说:“老婆,如果我们自己做老板,那有多棒!”太太回道:“赶快睡你的觉吧,天快亮了,你还在做梦。”太太一大声,阿基师就小声。 赚那么多钱,阿基师生活却节俭得可怜。每个月生活费台币三千块(人民币不到一千元)。他说,少一点物欲就行了。人家买香奈儿5号,一瓶那么贵,何必呢?看电影?回家电影台就有阿。他的观念是“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更香”。男生克就吃饱,女生克就吃饱。很多大师傅肚子都很大,阿基师却是苗条的身材。因为他吃东西也节制,而且是挑剔的。比如吃葡萄,除了杆,其他99.9%都要吃掉。比如他做菜不用番茄酱,是把番茄切开,用汤匙将茄囊汁做点缀、提味。他会说:那个才是叫真正的原味嘛。 阿基师有这么多诀窍,不藏、不埋,他全做成节目写成书传播出去了。他认为,学问这个东西,就像一个肥料,是要遍地播撒,开花结果的。“我还能活多久?”他说,“等我挂了,变成云烟,就什么都没了。”人就像海绵,得把自己掏空了,才能吸收更多的能量。 诀窍传出去了,刀,也是要传的。 这么多年,阿基师很少换刀。“刀不能换的。经常换刀,就可以经常换老婆了。”刀之于厨师,就像枪之于军人。到了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再把刀送人。给朋友,徒子徒孙也行。总之是要传下去的。阿基师的刀,是沾了他人生故事的——“因为一把刀,我大开鸿运中头彩,我品质口碑名声冲四海,我收入冲九天,我的老婆开心似神仙。”——刀在人在。 跟他最长时间的一把刀,三十多年了,如今还摆在家里。他永远都把它磨得亮亮的,像观音菩萨供着,有事没事拿起来,摸一摸、动一动。阿基师的灵气附着在上面呢。 他永远告诉自己,阿基师的精神不会灭的。 鸣海登 刀是魂,在某种意义上比老婆女儿重要 日本人,60岁 外滩源壹号“空蝉”怀石料理料理长 曾在日本关西地区大阪、京都、奈良修行怀石料理。而后于小田原希尔顿日本料理与马来西亚希尔顿担任料理长。参与制作日本天皇家宴,表演古式庖丁仪式及技法,并收到天皇钦赐庖丁厨师刀。 中国人是一把刀走天下。在日本,需要两把刀。一把大的,一把小的。日本料理的每一种切法,都是规定好的。蔬菜一种刀,鱼是另一种刀。但每个厨师都有自己的心头好,鸣海登用的最多的,是一把特制的钢刀。他说,作为一名厨师,刀就是他的命。 厨房是个江湖。厨师们赖以生存的,除了厨艺,就是刀了。从这个角度看,日本厨师算讨了个小便宜。全世界最厉害的产刀之地,无外乎欧亚几个国家,而日本是行业翘楚。日本人造刀,是先打铁,再把刀刃镶嵌上去。在古代,用的是“水烧”的做法,刀浸在水里。现代的做法是“油烧”,品质会更好。鸣海登说,一把好刀的材质,必须是钢。他随身携带的那把刀,刀身上还刻着锻造者的名字。但造刀的人是一回事,用刀,是自己的本事。一个怀石料理厨师必须具备的能力,是熟练地运用各种刀,去呈现食材原有的味道。 但在日本学料理,是个漫长的过程。就像刀客,出来行走江湖,人们总会猜测他的师承和家学,却猜不到他付出了多少年。 鸣海登学料理,最初是因为饿。家里太穷,只有做厨师才可能吃到美味的食物。他出生在北海道附近的青森县,一个被海包围的地方。对父母来说,厨师、木匠,这种具有一技之长的职业,是金饭碗,不会被时代抛弃的行业。 他去了大阪学厨。但他的启蒙师傅有点管不住他。鸣海登那时性格火爆,是个叛逆的年轻人。师傅说,得把他送到一个更严格的地方去。也在大阪,做怀石料理的。他一学就是十五年,慢慢地认识了好多厨师和朋友。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远藤十士夫——他后来成为日本最传奇的料理师之一。 远藤十士夫推荐鸣海登去学习庖丁仪式。怀石料理,是美食界最具份量的日本料理。据说起源于光孝天皇,他为了供奉掌管料理的菩萨,命藤原去准备一道料理。如今庖丁仪式的道场,仍会有菩萨和鼻祖的画像。后来藤原改姓为四条。鸣海登所学的庖丁仪式,就来自四条司家。 庖丁仪式并不是所有厨师都能去学的。那需要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机遇,还需要有料理长的资格证书。鸣海登学了十年。对他来说,远藤十士夫是他人生中的关键性人物,是江湖上传了很久的顶尖高手,碰到了,学得几手,已是福气。如今远藤十士夫已77岁,鸣海登偶尔还和他保持联系。 在鸣海登学厨的那个时代,刀法不是学来的,是偷来的。 师傅是从来不主动教的,也没有手把手教徒弟这种传统。鸣海登只能看别人怎么做,然后模仿者学。他当学徒的前三年,是洗盘子。接着两年,是帮师傅准备菜,这时他就暗暗记下鱼、菜等所有食材的名字。然后才有机会上烤台做东西。烤台之后是主台,主台之后就才能去做刺身。到了刺身这一步,意味着你已是店长级别的人物了。但是上述所有的过程,没有人教你,你只能偷偷去看前辈师傅如何去做,然后在空余的时间,买些食材或者是店里不用的食材,慢慢练习。“所以对我来讲,每一个技艺都很难。”鸣海登说,“因为没人教过我。” 有一次,昭和天皇希望四条司家去表演一下庖丁仪式。当时选了四个人,鸣海登幸运地成为其中之一。天皇看完表演,非常高兴,给出场的四个人每人送了一把皇室特质的刀。那把刀很特别,刀鞘也是特质的,上面涂有一层发亮的特质漆。刀鞘上刻着天皇家族特有的十六花瓣表菊纹徽章。 有了这把刀,鸣海登在江湖上有了地位。 在大阪待了十五年后,鸣海登去了小田原,那里的希尔顿酒店刚开业。八年后,又去了马来西亚的希尔顿。有次回日本,一个朋友说上海有个工作机会。他对上海一直很有兴趣。如今,他已在上海工作了两年。厨师这一行就是如此,居无定所,无论多少年,陪伴身边的只有一把把刀。 对普通人来说,刀只是武器,用来攻击或者防御,但是对一名料理人来说,不同的刀,能展现不同食物的最本质最纯粹的原味。“即便抛开了料理人身份,刀也是除了生命之外我最重要的东西。”鸣海登说,“某种意义上,比妻子女儿更重要。”在日本古代,刀是和武士密切相关的。刀是武士的魂。鸣海登说,现在,刀就是他的魂。 清斐 文思豆腐的人生哲学 扬州人,36岁 曾任上海著名的墨西哥餐厅MAYA的行政主厨,在此之前,他也已在海内外游学十余年之久,吸取了各方之长。灵感和造诣深受精致法餐,传统淮扬菜,和新式南美美食的影响,菜品创作大胆而有心意。 清斐学厨时,练刀功有好几种练法。比如练切片,师傅搬来一大筐土豆,堆一米五高,他花两个小时才能把所有土豆削好。比如砍玉米,砍着砍着就睡着了,刀切下来砍到手指。再比如,切姜丝。姜丝切完之后泡在水里——然后把所有姜丝穿针。扬州还有个名菜,叫大煮干丝,原料是淮扬方干,刀工要求极为精细,需要切干片。切成18片算及格,28片满分。清斐切到了30片。 最难练的是文思豆腐。把豆腐放水里,切成丝。清斐没事就买个豆腐回家练。 清斐这名字,听起来像东南亚人。但他其实是江苏人。他说,每个厨师都是从吃货开始的。他爱吃到什么地步?大家都去考普通高中,考大学,他却觉得学习数理化不自由。还是有门手艺好,可以边学边吃,还能开餐馆。 在学校,他学的就是淮扬菜。这个菜系注重形,什么都要求精细,对刀功的要求很高。他想着以后自己肯定是做淮扬菜的,天天练。没想到毕业后,直接去了海南的索菲特酒店。以前学的,派不上用场了。那里主做西餐,西餐对刀功的要求,不像淮扬菜那么夸张,但另外的问题来了。 比如煎鸡蛋。清斐觉得那很简单啊,用平锅倒油,然后炸成很脆的金黄色就好。端出来一看,大厨说,这种鸡蛋怎么拿得出手?清斐才明白,西餐中的早餐煎蛋,其实是很难的,要求没有气孔,煎出来是白的。因此不能太多油。所谓的“冷油热锅”——说起来容易,煎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清斐煎了七、八个月。 这个酒店的大厨,是法国人。有次清斐和他做一个晚宴,每道菜都做得很精致。清斐突然发现了西餐的美。“好看。”他说,“那时没想其他的,就是特别好看。”清斐开始学做西餐。他觉得西餐的摆盘特别漂亮,每一道菜,都像一件艺术品。但一个中国人突然学西餐,味道是很难把握好的。几乎是无意识的,他渐渐偏离了方向,只在乎形状和排盘。然后清斐就遇到了BradTurley,一个美国大厨。 Brad告诉清斐,外观好看,是顾客想去接触西餐的首要条件,但如果要深入了解,还得靠味道。清斐的理解是,这就像谈恋爱,长得好看的自然容易吸引人,但是深入了解后,内涵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菜肴的外形和味道是相辅相成的。Brad的出现,让清斐对西餐的认识有了质的改变。 主厨都是脾气不好的人,Brad也如此。清斐以前不太明白,他自己算是温和的人。但有一次,一个小工把胡椒粒撒在地上了,清斐自己跑去整理。Brad冲过来用英语一阵狂骂。他说,“首先,厨房是自己的地方,把厨房弄得又乱又脏当然不对;其次,你是我的副手,没有管理好下面的人,也是你的错。但整理厨房不是你的事,你的工作是配合我如何把菜做好。”清斐觉得条条都有道理。他也逐渐明白为什么主厨都是坏脾气,从早工作到晚,神经一直处于紧绷状态,始终绷着一根弦。如果你不小心触碰到它,自然是会反弹的。 每一个主厨,都有自己的武器。清斐最厉害的武器,还是刀。他可是练淮扬菜练出来的。 即便不是厨师,清斐也会喜欢上刀。“什么感觉呢?”他说,“冷、酷。”除了用刀,他还会收藏刀。世界上最好的刀,大概就是德系和日系了。德系刀追求的是厚重、手感,日系刀强调轻便、锋利。这可能和冷兵器时代的作战方式有关。清斐的手很大,拿德国刀似乎更顺手。 有了刀,刀法就可以任意变幻了。 清斐是自创刀法的人。他擅长把两个最不相干的食材放在一起,做出既好看又好吃的菜。在这一点,“吃货”就发生作用了。他总是到处去吃,尤其喜欢澳洲。因为澳洲菜融合了很多的亚洲元素。那里有很多开放式厨房。他就坐在厨房前的吧台吃,边吃边学,找灵感。 很久以前,有个主厨对清斐说过一句话,“选择这一行,要想清楚,你有没有做一件事做50年的准备?”清斐现在知道,这是厨师界的真理。即便做了主厨,也需要不停的学。所谓学无止境。为此,他还去一家墨西哥餐厅做过主厨,那是个冷门菜系。但因为冷门,才新鲜。 在清斐所有自创的菜品中,他最喜欢的是一道日料,味增银鳕鱼。日本料理也是最讲究刀功的。对清斐来说,把刀功和刀法结合在一起,江湖就可以任意闯闯了。 清斐的厨师生涯,起初是一步一步,按部就班进行的。无奇遇,也无奇人。“算是平稳。”他说,“也可能是平淡。”清斐的学徒生活,是中国大多数厨师的缩影,是在平庸和非凡之间的短暂停留。有点儿像武林中的名门正派弟子,基本功有了,却无大招。最多,也只能算是弟子中的佼佼者。但入了江湖,是容易吃亏的。 Maxime意大利人 刀如人,除了锋利,还得舒服。 从师于世界米其林三星厨师MartinBerasategui,上海的RestaurantMartin位于徐汇公园的老洋房里,而Maxime在这家餐厅担任了多年行政主厨。 早年,还在西班牙时,Maxime下班后就喜欢磨刀。刀呢,就像人生。他说,还是锋利一点好。 他学厨。师傅在西班牙享有大名,开了个享有大名的餐厅RestaurantMartin。Maxime主要做鱼。师傅说,鱼对刀的要求很高,随时随地都得保持锋利。师傅送过他很多刀,把把都需要磨的。师傅是他的启蒙老师,像父亲,很固执也很坚持。虽然没多大耐心,但宽容,犯了错也不要紧,因此很多人都想到这里学厨。师傅对厨房有种狂热。有次早晨刚做完手术,下午就回了餐厅,脸色苍白,一直冒冷汗,但仍忙个不停。“好像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对烹饪的爱。”Maxime说。在这一点,他受师傅的影响很深。做厨师,得一辈子爱食物。 Maxime是生在法国的意大利人,这两个国家盛产美食家。他从小长在乡村,周围遍布传统美食,做手工奶酪的,做红酒的。吃,是享受。做吃的人,还会多一层享受。他年开始学厨。那时没多少人想当厨师,觉得赃,浑身是汗。 别人都在Party,你却是那个负责Party食物的人。所以马克西姆最先学会的是如何抵制诱惑,把精力放在厨房。但厨房也有厨房的问题,他得学会和人相处。“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坏家伙,不尊重你,可能会说一些很粗鲁的话,但你只能学会闭嘴,学会低头。”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锻炼人的过程,塑造你的性格,让你变得更强大。” 在厨房,刀才是Maxime最好的朋友。契合得好,刀就像手的延伸,是身体的一部分。但如果相处不当,刀也会带来伤害。他受过很多伤。手指上,胳膊上,有次开生蚝还割伤了肚子。“我对他既爱又恨。”他说。他亲切地称呼自己的刀为“Him”。 一把好刀有多重要?比如你需要剁20斤洋葱,如果刀不锋利,那就像噩梦一样,你会一直掉眼泪。他人生第一把刀,是母亲送的。母亲送的第一件厨房用品,其实是件便宜的白衣服,她不确定儿子是否真的要做厨师。马克西姆那时只能找别人借刀用。借久了,母亲看出了他的执着,买了一把刀,跟他跟到现在。此后他拥有超过一百把刀。其中一些可能已经坏了。有把很好看的刀,被同事弄坏了,他为此哭过。“那时没多少钱,所以刀对我的意义很重要。”他说。但慢慢地,他也会明白,一把刀,不会永远和你在一起。到后来,他偶尔也会送朋友刀。送的时候,刀尖朝向自己。 并不是每把刀都适合自己。每个人的手不一样。别人握着舒服,也许你握着很难受。时间久了,厨师们会越来越懂自己的需要,也会越来越挑剔——刀呢,还真的挺像人生——除了锋利,还得舒服。 几年前,师傅把餐厅开到了上海。Maxime跟了过来。新餐厅开张,他忙个不停。每天都有供应商到面前推销他们的橄榄油、火腿、奶酪、红酒。每天都一样,无聊极了,而且是被琐事消耗至死的无聊。在厨房,他和20个厨师共事,却没人感觉到刀的重要性。很长时间,他都快忘了刀这个朋友。在上海,他也很难找到质量与之前相仿的刀。 但现在,那些厨师中至少一半的人告诉他,他们也想要一把好刀。 Maxime注册了一家卖刀的公司。他卖锋利的刀,尤其推荐日本的刀——日本人很专注于寻找世界上最好的材料去做刀。他说,卖刀,不在赚钱,在于交流。对一个年轻厨师来说,即使没有多少经验,但如果有几把好刀,也许会获得更好的机会。因为,刀和人相似,什么样的人,交什么样的朋友。看刀,也能看透人。 第二季柏林特辑 即将在我们网站“发射站”上线 我们采访了20位柏林人关于...活法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inglanga.com/blgx/13878.html
- 上一篇文章: 四月圣花,地涌金莲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