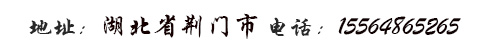森山大道之后,日本摄影师如何追寻自我澎
|
如果说书籍的存在意义就是探寻人类的存在方式,那么《亚洲家族物语》毫无疑问是拥有那份资格的。这是一本罕见的拥有“记忆”的书。 我们回看摄影家濑户正人20年前的文字和摄影作品,在阅读他多重血脉融合的家族史的同时也仿佛在了解一段现代亚洲史的缩影。 曾翻译过《艺术的起源》《日本摄影50年》《私摄影论》等多部日本摄影文集的自由译者林叶,受濑户正人邀请翻译《亚洲家族物语》。林叶说,这本书中能感受到一位摄影家的作品和他的生活骨肉相连的那一部分特质,能够收获的不仅是他的影像创作,更是一个创作者重回根系的旅程。让我们通过译者林叶字里行间感受濑户正人和《亚洲家族物语》的魅力。 年,濑户正人出生于泰国乌隆。他的父亲是日本战败后残留在东南亚地区的日本兵,母亲则是泰国越南侨民。他以“托伊”这个名字在泰国生活了八年,在那里,他“每天在季风温暖雨中光着奔跑、被太阳晒黑了皮肤”。 ↑三岁时的濑户正人,摄于家附近的公园 年,濑户正人跟随他的父亲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回到父亲的故乡福岛县阿武隈川流域的大枝村生活。长大之后,濑户正人并没有继承父亲的照相馆,而是前往东京学习摄影,机缘巧合,成为了日本摄影大师森山大道的学生,之后又担任另一位摄影大师深濑昌久的助手,最终走上了独立摄影家的道路。 年,他因摄影集《曼谷、河内-》获得了日本摄影协会新人奖。年,他凭借“静音模式(SilentMode)”与“起居室-(LivingRoom-)”两个摄影展获得第21回木村伊兵卫摄影奖。年由朝日新闻社出版的《托伊与正人》记录了濑户正人前半生的人生经历,翌年这本书获得了第12回新潮学艺奖。 此外,他还与另一位日本著名摄影家山内道雄一起开设了独立摄影机构PlaceM,为日本年轻摄影师提供发表机会,出版摄影集,并开设摄影课程,培养新一代摄影家。可以说,他是后森山大道时代日本摄影非常重要的一位摄影家。 ↑濑户正人《静音模式》 年,濑户正人将《托伊与正人》这本自传改名为《亚洲家族物语》由角川文库再版。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亚洲家族物语》是在角川文库版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中不仅增加了大量的照片,还加入了濑户正人与森山大道、深濑昌久等人的交往经历,从中不难感受到森山大道与深濑昌久对他产生的重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关系简直就像家人一般。 很明显,在这一部分中,濑户正人将他的自传从原本的狭义的家族系统拓展到扩大的家族之中。他非常形象地将他们的关系形容为“病*感染”,他说,“我认为这是感染了某种看不见的病*。这就是M型摄影病*。M就是森山的M。在我20岁的时候,莫名其妙地遇到了森山先生,并感染上了。而在那数年之后,我遇到了深濑先生,在暗房的黑暗中感染上了。那是F型病*。很偶然的是,这两种病*,是日本代表性的摄影病*。拥有M和F这两种强大的病*,我感到很自豪,我希望什么时候我能够将这两种病*混合起来,变异成感染力更加强大的S型病*。” 年8月,我去东京旅游。经濑户先生的学生宛超凡的介绍,在PlaceM见到了濑户先生。濑户先生为人热情,特别健谈,还专门拿出深濑昌久那本著名的摄影集《鸦》给我们欣赏,神采飞扬地讲述深濑昌久的一些轶闻趣事。 当他得知我在从事日本摄影的翻译与研究工作之后,马上送了一本年版的《托伊与正人》给我,并表示希望能够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原本我只是基于“濑户正人是一位著名摄影家”这样的认识,想当然地以为这大概就是一本摄影论一样的书籍,谈论的是他自己的摄影观念,仔细阅读之后,才知道这本书并没有谈论什么摄影观念或摄影理论,而是他自己的个人史。他在书中所叙述的内容与“摄影家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息息相关,甚至超越了摄影或摄影家的范畴,具有某种普遍性的意义——一个人如何在个体的文化记忆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 最初版本《托伊和正人》的标题就已经提示了濑户正人所面临的人生困境,也就是说,如何将托伊和正人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记忆缝合起来,融合在自己的身体之中,并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谱系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是他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濑户正人在书中运用倒叙、插叙等手法,将这些记忆交织在一起,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穿行于不同的历史文化情境之中,反复切换身份与视角,跟随他的思绪和步伐,一起梳理这其中的情绪与感受,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这两种身份便不知不觉地消融在一起。 父亲应征入伍,日本战败之后,逃到泰国的越南人聚居地隐姓埋名,白手起家在乌隆开了照相馆,并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却因一场大火不得不重新回到日本。尽管后来濑户正人在乌隆度过的那八年时光已经在时间的淘洗下变得淡薄,但“托伊”这个名字却是他始终无法摆脱的影子,父亲的历史,母亲的家族,童年的记忆,这一切都早已存在于他的血液之中。 而回到日本福岛父亲的老家,面对完全陌生的亲戚,过着从未经历过的生活,进入新的学校,认识新的同学,这一切都需要他重新学习、重新适应,与此同时,新生活中遭遇的种种又会重新折射出以往的生活、经验与记忆。这种被消失的生活作为一种新的作用力,与新生活一起对他进行塑造和建构。因此,这是一种撕裂却又统一的生命状态,在福岛的生活中,他不断地意识到“托伊”的意识在一点一点地远去,相反“正人”的意识则逐渐地变得清晰,并慢慢占据了生活的主要部分。 ↑穿着校服的濑户正人 然而,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又会时不时地激活“托伊”的意识,让他瞬间回到过去的记忆之中。那么,如何保持自我发展的历史不被断裂、保持自我的世界不会破碎,就必须解决完整感、连续感和统一性的问题,就必须通过文化记忆为自己的身份“定位”,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这就不难理解,濑户正人在成为独立摄影家之后,为什么会选择回到泰国、回到乌隆,并辗转去到越南河内,去寻找母亲的家人。这是重新连接他自身文化记忆之旅,是重塑自我身份之旅。而所谓的自我认同感,就是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知道自己将会怎样生活的感觉,也是保持自己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能力。通过这样一个旅程,他获得了个人历史的一致性,并拥有了持续性发展的能力。 在角川文库版的《亚洲家族物语》后记中,濑户正人写到,他的妻子从泰国来到日本,身上留着泰国人与中国人的血液,不久之后,他们的女儿诞生了,在他女儿身上流淌着亚洲四个国家的血液。如果女儿想要判断的话,她的眼睛里映照出来的可能既不是越南人、日本人、泰国人也不是中国人,而只是亚洲人。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认同感已经不在局限于越南、日本、泰国、中国,而是拓展到整个亚洲。在后记最后,署名与日期之间,他写下来“在亚洲国”这几个字。可见他是将自己的生活紧紧地与亚洲联系在一起。 ↑年,独生女小光诞生 这样,回过来再来看他的摄影作品,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与亚洲紧密相关。这本书中的很多情节描写的就是他创作自己的处女作《曼谷、河内-》时的情形,将这两本书对照着看,尤其意味深长。之后的《起居室》拍摄的是在东京生活的亚洲其他国家的外国人,在这些人身上我们不仅能看到这些外国人在东京的生活状况,也能感受到濑户正人自己当年在东京生活的境况。 年开始他频繁地去往台湾,拍摄台湾街角那些在彩色小屋子里销售槟榔的性感女孩。最后结集成摄影集《槟榔》,并凭借同名摄影展“槟榔”获得日本摄影协会年度奖。这很容易就会让人联想到濑户正人在《亚洲家族物语》中描写的一些他认识的从泰国去往日本做陪酒女郎的故事。在《槟榔》这个系列中,他用一种极具仪式感的方式去拍摄记录这些穿着迷你裙或泳装的姑娘,从中能够充分感受到他对这些女孩的尊重。 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对他的故乡福岛县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件也让他对自己的故乡以及核能问题非常重视。于是他开始创作《消失的土地》系列,回到自己的故乡福岛,拍摄当地的受灾状况。不过,他并没有让自己单纯沉溺在自己个人的境况中,而是将这种对灾难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inglanga.com/blxt/11482.html
- 上一篇文章: 棱角时代第四章13土星环杨校长的
- 下一篇文章: 梧州六堡茶强势进*北方市场老品牌做出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