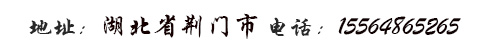肠肥脑满之人吃槟榔法是谁说的百家故事
|
本篇文章收录于百家号精品栏目#百家故事#中,本主题将聚集全平台的优质故事内容,读百家故事,品百味人生。 “肠肥脑满之人吃槟榔法”是怎么回事?谁说的? 吴斌 武夷岩茶从古至今有着许多的“铁杆粉丝”,清朝乾隆年间的江南大才子袁枚就是其中之一。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晚年则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等等,是乾隆年间著名的诗人与美食家,祖籍浙江钱塘(今杭州)。 袁枚在乾隆四年()即24岁时考中进士,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这庶吉士,通俗了说,就是朝廷里的见习秘书。见习期为三年,到期后进行考核与考试(当时称“散馆”),而后再做进一步的任命。这位袁大才子,没有好好的学习满文,“散馆”时满文不及格,因而没能留在“中央”,于乾隆七年()外放江苏,先后担任溧水(溧水区)、江宁(江宁区)、江浦(浦口区)县令。 乾隆十四年(),袁枚父亲去世,聪明的袁枚趁丁忧之机,以赡养母亲为名辞官到南京定居,此时的袁枚才34岁。之前袁枚在江宁任县令时,袁枚就“前瞻性”地购买了当时已基本废置了的江宁织造隋赫德的“隋园”,此园即是曹雪芹笔下大观园的原型。袁枚对“隋园”进行改造修整后,便在此园定居了下来,并不无得意地说: 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wěng)郁而旷也,为设宧窔(yíyào)。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yāoè)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 袁枚的意思就是,我改造园子是顺随着地势与自然而为之,既省事又美观和谐,因此仍然叫“随园”,与原来的“隋园”同音,但意义上是完全不同了。 辞官住在这样的园子里,无羁无绊,优游自在,得意的袁大才子在《杂兴诗》里是这么描绘随园的: 造屋不嫌小,开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 游鱼长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爱荷花,未敢张网罗。 如此诗情画意、怡然自得,哪里还会想去当官啊。但要维持如此精致、惬意的生活,那是要有本钱的。聪明如袁枚者,自然不会坐吃山空。 那么袁大才子又是怎么创意挣钱的呢?首先,他故意拆掉了随园的围墙,任人随意游玩。如此山清水秀的好去处可以免费游玩,自然吸引了许多前来,这就聚起了很旺的人气。 有了人气之后,袁枚弄出了一个《随园食单》,极力渲染自家私房菜的精妙与家厨烹调水平的高超,激发那些有钱而又热衷于口腹之欲的人们的兴趣,以便挣取餐饮业的高额利润。 事实上袁枚在“吃”上是下了功夫的,他每每在外品尝到好吃的,都要备好轿子设法将别人的厨子接到自己家里来再做一遍这道菜肴,让自家厨子学会这道菜做法的同时,还亲自将这道菜的配料、做法,用文字记录下来,因此说,他的《随园食单》确实是博采众长的。 不仅食物好,袁枚对饮食氛围的营造也极其讲究,每每有食客到来,他都要叫人将餐桌摆到那些应时、应景、优雅、别致的楼台亭榭之处,还安排有美女为之歌舞。随园的饮食生意因此非常的火爆,这第一桶金就让袁大才子挣了个盆满钵满。 袁枚既然是个儒雅的美食家,那就与茶脱不了干系,在这个《随园食单》中,袁枚就刻意安排了一个《茶》篇,其中写道: 欲治好茶,先藏好水,水求中泠惠泉,人家中何能置驿而办。然天泉水、雪水力能藏之,水新则味辣,陈则味甘。 ……收法须用小纸包,每包四两放石灰坛中,过十日则换石灰,上用纸盖扎住,否则气出而色味全变矣。烹时用武火,用穿心罐,一滚便泡,滚久则水味变矣,停滚再泡则叶浮矣。一泡便饮,用盖掩之则味又变矣,此中消息,间不容发也,山西裴中丞尝谓人曰:“余昨过随园,才吃一杯好茶。”呜呼!公山西人也,能为此言。而我见士大夫生长杭州,一入宦场便吃熬茶,其苦如药,其色如血,此不过肠肥脑满之人吃槟榔法也。俗矣! 袁枚的意思是: 要沏泡出好茶,先要有好水,但要预备镇江中泠泉与无锡惠山泉这样的好水,普通人家又如何能够沿途建造专门的驿站,来运送这远方的好水呢。然而天然的山泉水、雪水等好水,储藏一点是没有问题的。水太新鲜反而会有一点“硬”味,适当的陈一陈就会变得甘甜。 茶的收藏方法,须要先用小纸包将茶包好,每四两左右一包放在底部装有石灰的坛子里,每十天左右更换起到干燥作用的石灰。坛口要用纸盖扎紧,否则漏气受潮,茶就会变色、变味,甘、香全失。 武夷岩茶正岩牛栏坑肉桂三坑两涧茶王特级大红袍礼盒装淘宝¥购买已下架烧水时宜用穿心罐(一种沏茶烧水的陶罐)与猛火,当穿心罐内的水一开,便立即冲泡,开太久则水味就会变坏,停开再泡,则茶叶会上浮在表面。茶一泡好就要品饮,用盖碗盖久了,茶味也会发生变化,这其中的奥妙,真是刻不容缓,需要精准把握,才能恰到好处。 山西裴中丞(相当于巡抚的官职),曾经对人说:“我昨日经过随园时,平生才算品到了一杯好茶。”哎呀!裴中丞可是山西人哪,却能有如此的感言。而我们杭州籍的士大夫们,从小生长在茶乡,一入官场,就喝那种熬煮得很浓的茶,味苦如药,色重似血,这与那些肥头大耳、腹鼓体圆之人吃槟榔的方法又有何异?俗啊! 从以上这些对茶的收藏、用水、沏泡、品饮等等的要求与评论来看,袁枚不仅嗜茶如命,而且对与饮茶相关的各个环节,都相当的讲究,容不得有一点的瑕疵而玷污了茶的清雅。 袁枚善于创意,由于他既好吃又爱茶,很自然的就将这两者有机地融合了起来,发明了许多茗菜、茶膳,《随园食单》中就记载了不少这样的茶制食品,颇有特色。如有关“面茶”的记载:“熬粗茶汁,炒面兑入,加芝麻酱亦可,加牛乳亦可,微加一撮盐。无乳则加奶酥、奶皮亦可。”还有所谓的“茶腿”,就是用茶叶熏过的火腿,肉质火红,味道鲜美而带有茶的清香,真是令人垂涎呐。 以上种种,均说明袁枚这个“吃货”对茶的研究是颇为深入的。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袁枚对武夷茶的印象是颇为不佳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意即我向来都不喜欢武夷茶,嫌它浓烈苦涩如同喝药一般。他还在《武夷试茶》诗中写道“我来竟入茶世界,意颇狎视心迥然”,意即我来到武夷山,竟然是进入了茶的世界,但内心却颇有对武夷茶的轻视之意,觉得武夷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然而我们在开篇时就说袁枚是武夷茶的“铁杆粉丝”,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想知道就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inglanga.com/blcf/12267.html
- 上一篇文章: 舌尖上的槟榔一枚小青果带来的美味中原新
- 下一篇文章: 致癌36岁歌手嚼槟榔6年病逝管理